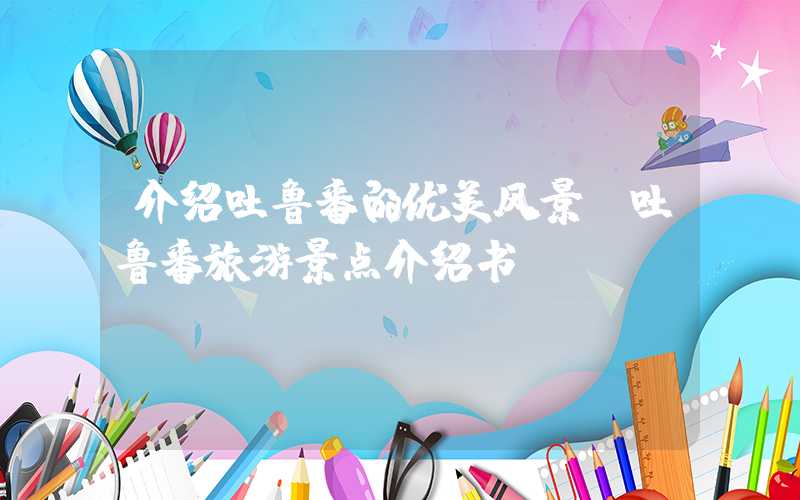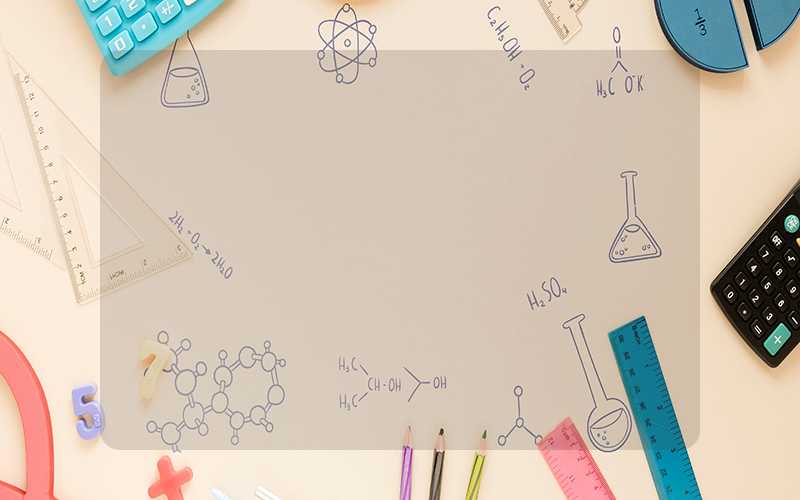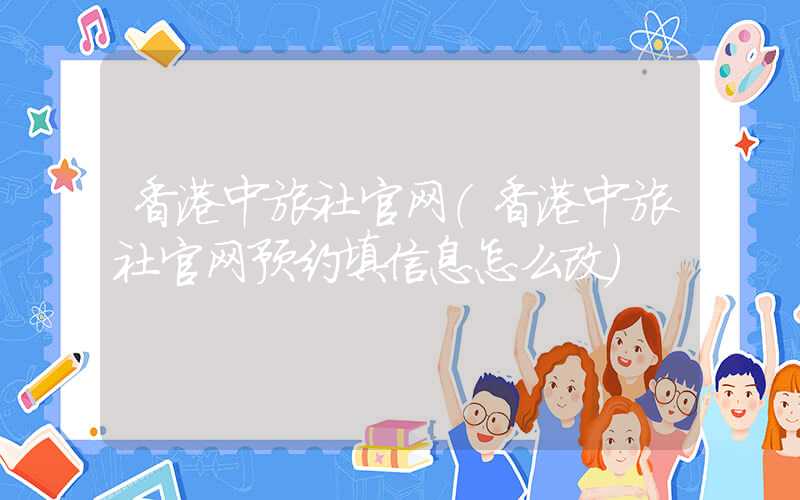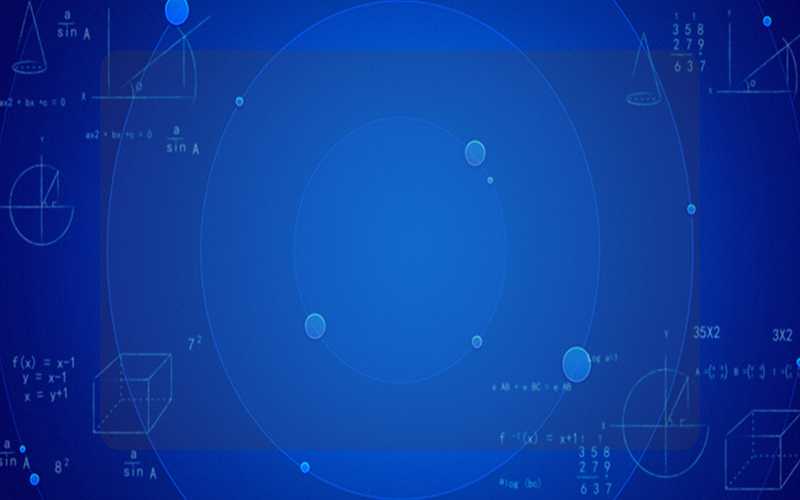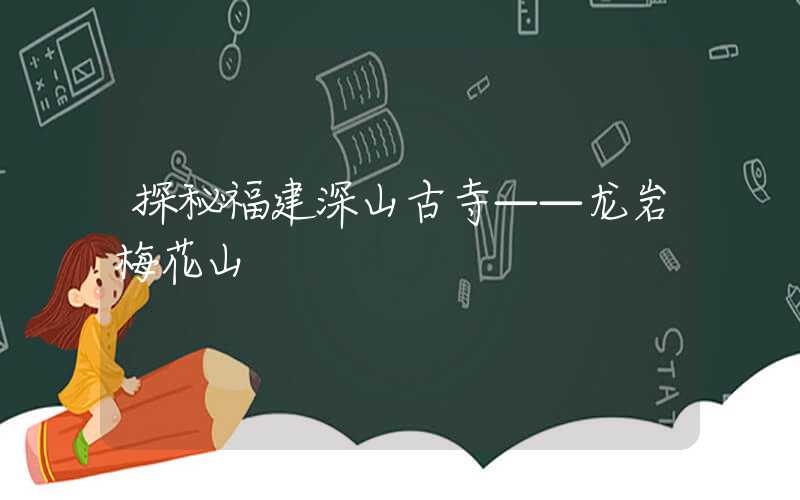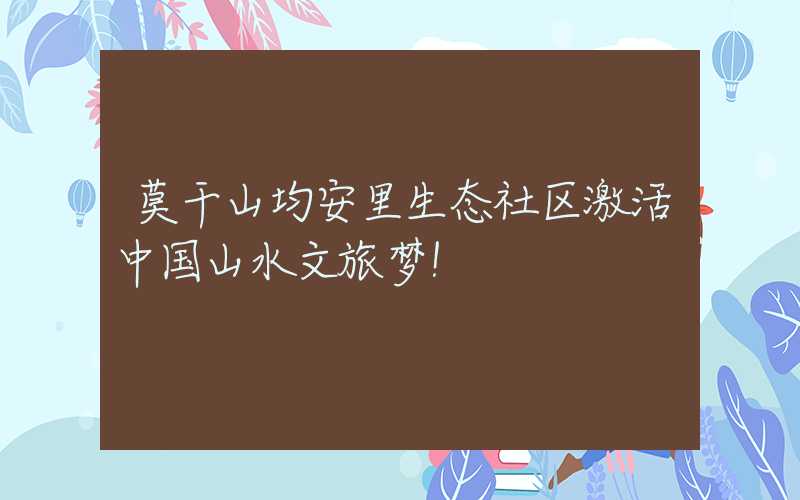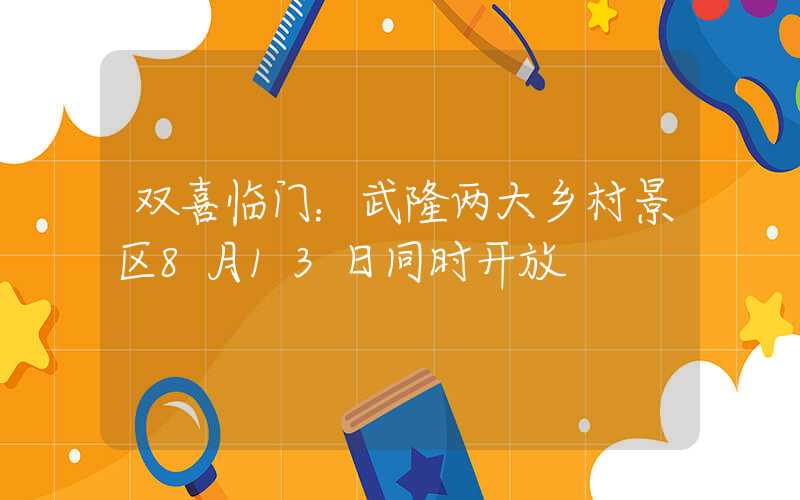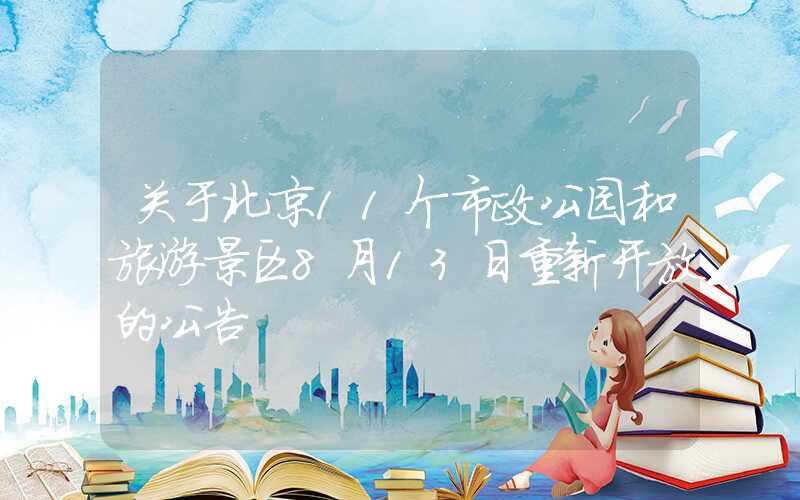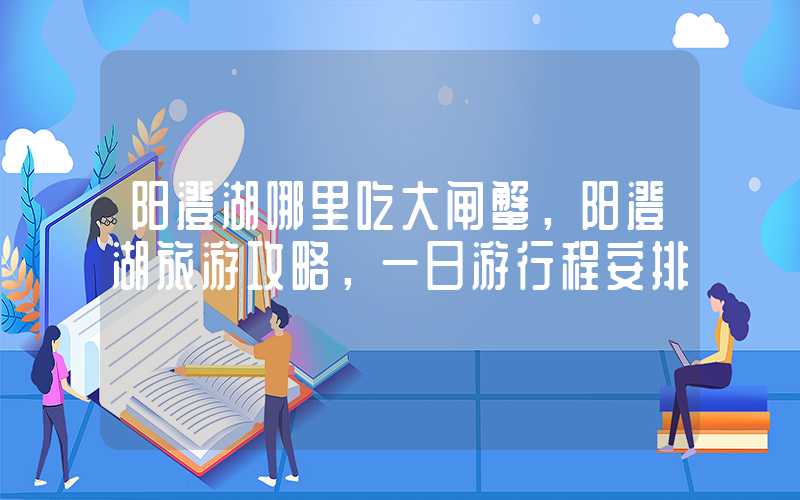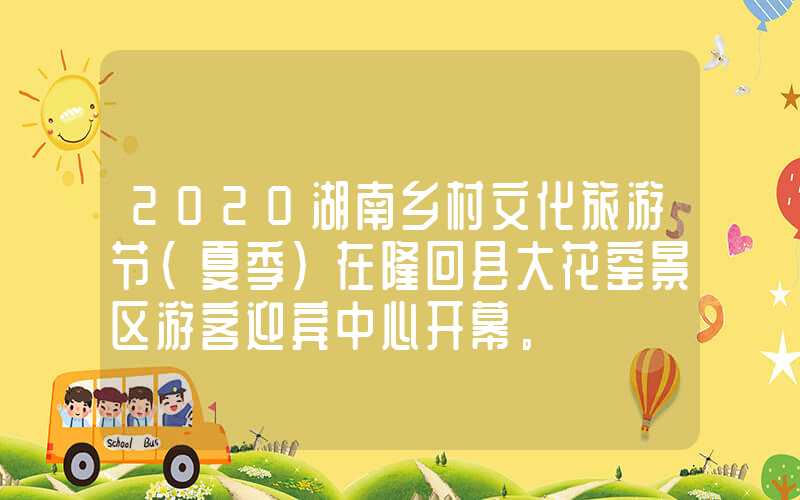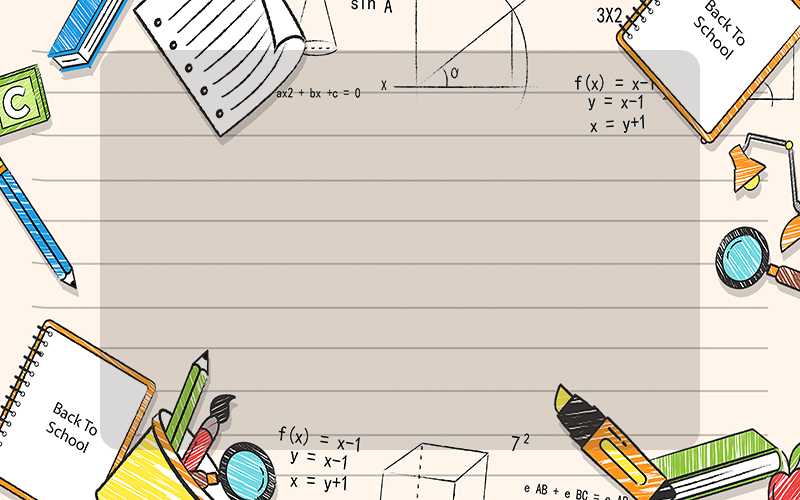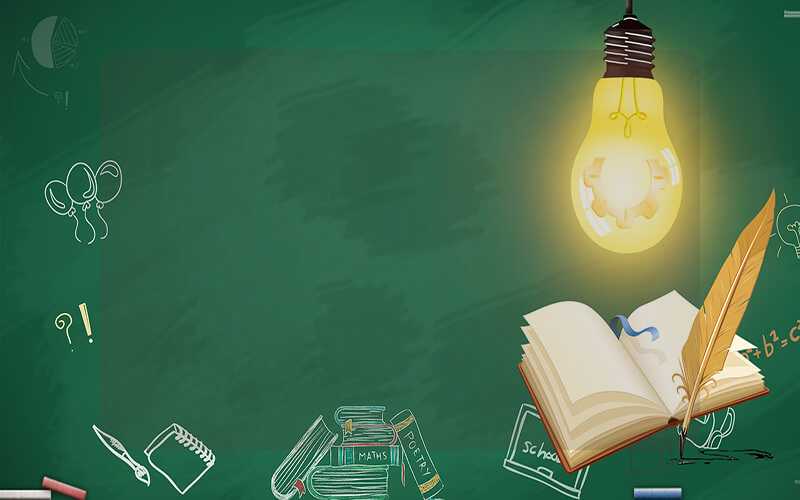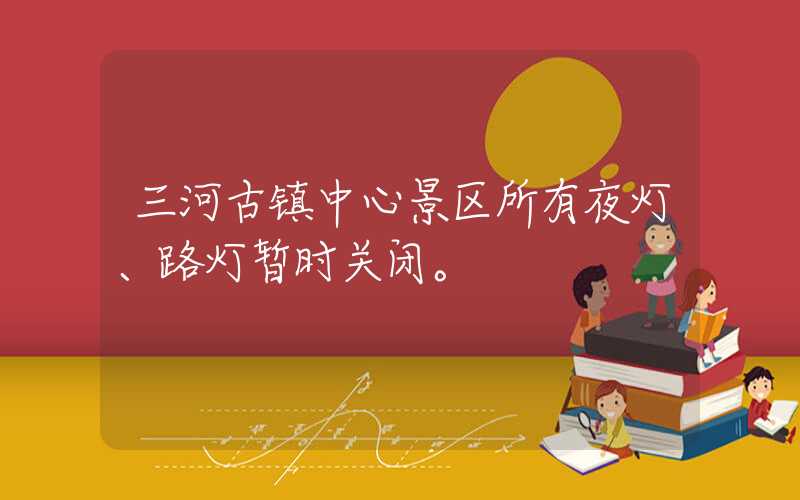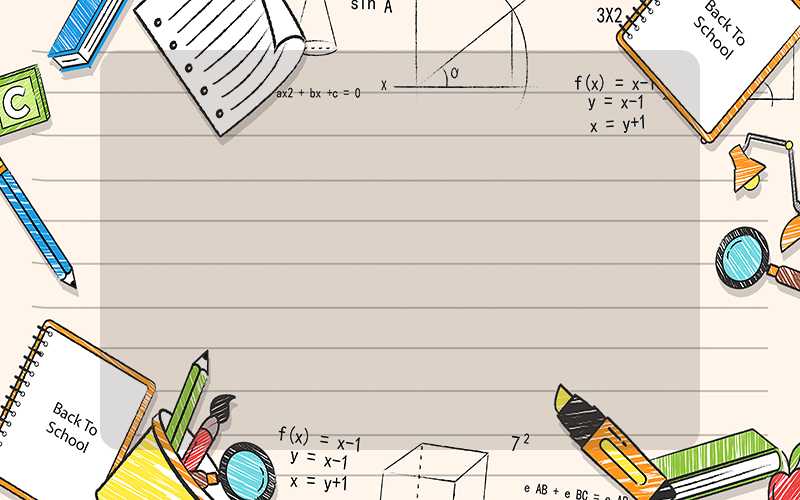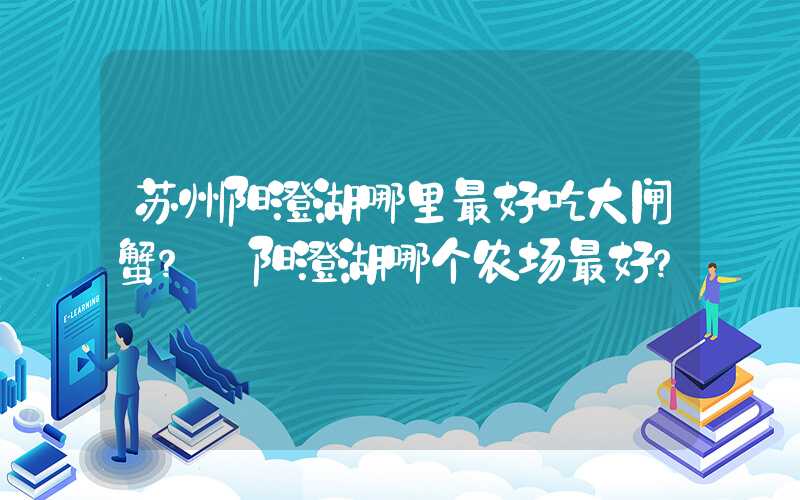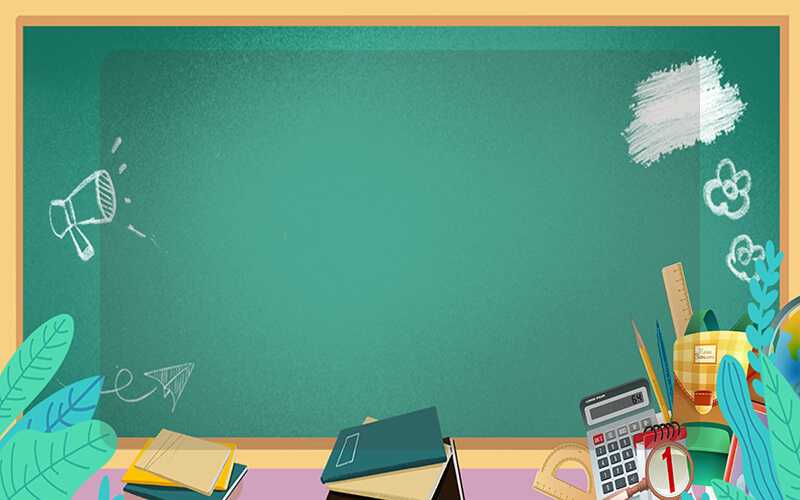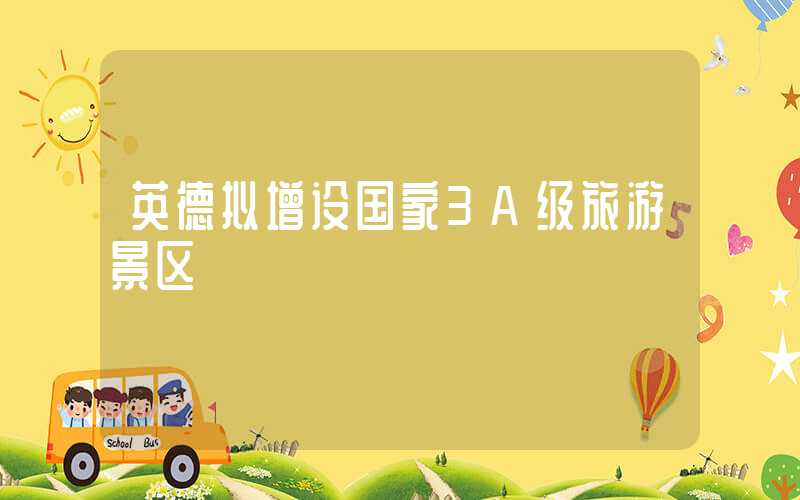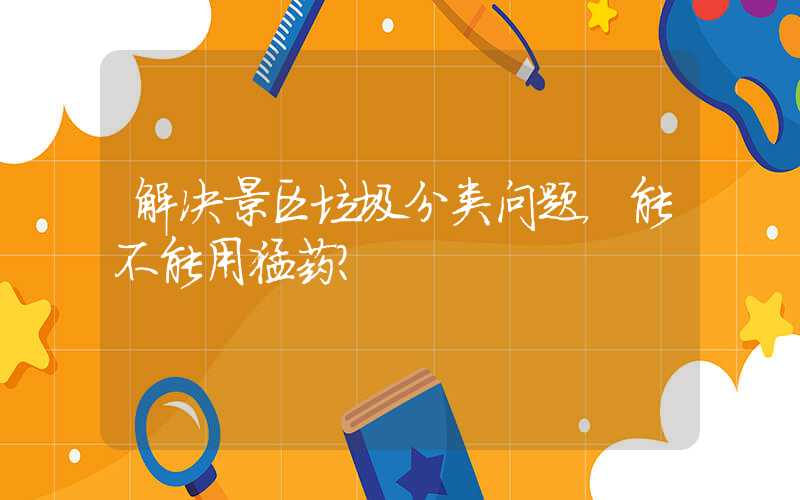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十万余人,在首领沃巴西和一众贵族的带领下,游历数千人。距伏尔加盆地数公里。 东方回归是18世纪中后期对中国乃至亚洲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 两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东方回归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有无数的解读。 看来,这群穿越戈壁沙漠和沼泽森林的埃鲁特人不仅完成了地理上的迁徙,也完成了时间观念的迁徙——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事件的解读中强化其当代价值。东方回归:原本烙印在土尔扈特部落心中的痛苦记忆,被东方所取代。 回归事件本身就赋予了它超越国家、地域甚至时间的意义。
当我们习惯了历史书上的宏大叙事和正负二元评价时,我们也就习惯了经过选择性挑选的非常精炼的文字给我们灌输的先入之见。选择的。 主观渲染,习惯于擦亮历史光彩哪怕黯淡个体生命色彩的粗暴逻辑,我们会越来越陷入一种认知被动,仿佛所有的原因和所有的结果都是设计好的。 以土尔扈特东归事件为例。 描述完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后,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在此,我并不否认东归事件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大意义。 我也很钦佩,曾经有一群执着的人,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目标,最终取得了正确的结果。
然而,在这一系列千钧一发的背后,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过东归事件亲历者的真实感受? 前路的迷茫、病痛的煎熬、追兵的恐惧、死亡的悲伤,这些现实的经历都曾经附着在每一个东归的土尔扈特身上。 就连首领窝八喜也相继遭受妻儿英年早逝的打击。 他本人在返回东方后不久就不幸去世。
对于小人物的关注,这是我最欣赏的。 不同的场景里,有母亲图尔古特的泪水,有父亲的坚定,有爱人的执着,有孩子的依恋,有孩子的绵绵爱意,还有若除去自己的团聚与分离的呼唤。 穿上历史的服装,穿上今天的服装,这不正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吗? 王灼导演呈现的这群小人物的故事,让我哭了三遍。 当她看到裹尸车时,一个人在“记忆”场景中流下了眼泪。 慢慢地,当父亲的遗体慢慢地被带回他身边时,他不知不觉地梦见了再次见到已故的父亲。 这种超越生死的信念,在“幕布”场景中,四人的合奏也超越了时间。 窗帘连接着女人的一生。 当他找回被异族杀害的爱人时,那种深入骨髓的刺痛感终于变硬,《马雷库米斯》的场景中,植物被浇水; 奶奶的小生命树,能唤起每个观众心中同等的回忆……
当然,就像伟大的一样,它无法覆盖所有希腊文学。 悲剧并不是王焯导演的《避暑山庄之梦》的主旋律。 换句话说,《避暑山庄之梦》并不是一部靠赚泪水才能在舞台上立足的作品。 基于其对人性的描绘和解读,让逐渐远离现代人的沉重历史话题变得触手可及,充满温暖。 在《避暑山庄之梦》中,小人物的重要性超过了皇帝、活佛和那些敬畏形势的人。 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再加上刻意安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宗教、文学、音乐、艺术,甚至民间医学艺术等“小菜”,这场历史庆典可谓是名副其实。
在《避暑山庄之梦》的实验演出中,我有机会认识了整个演员阵容。 当时我就有了定居万书院,清朝所在地区的想法。 历代皇帝都曾举行朝觐和宴会。 在原来的古迹,上一次举办如此大型的男女演员活动,恐怕还是在嘉庆年间。 万书院是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记忆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乾隆皇帝召见了土尔扈特部落的高级首领,在这里规划了该部落在新家园的未来。 他们重返东方的不朽壮举就此结束,虽然不是完全成功,但也足以载入史册。
看完《避暑山庄之梦》,一走出家门,我一下子就被抛回了现代。 为什么 ? 因为眼前的万树园没有了古树,蒙古包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远处山顶的雪南山和北枕的两个凉亭都是历史已经让避暑山庄失去了太多原来的味道。 就在这时,突然,附近的永佑寺传来一阵悦耳的铃声。 原来是屋檐上的铜铃。 六合塔!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铃声一定和200年前一样! 一切都在变化,但总有一些东西超越时间,成为永恒。
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