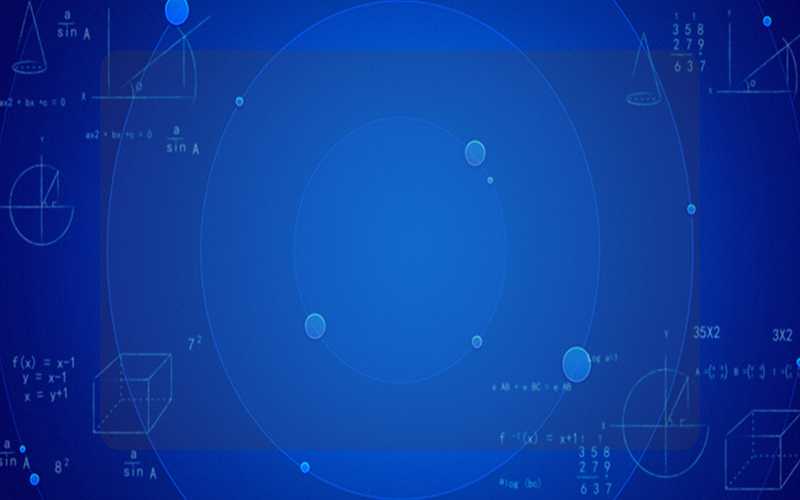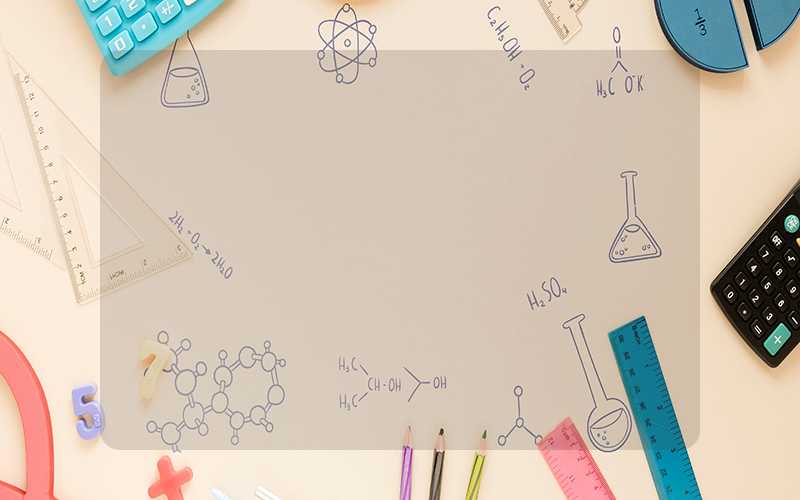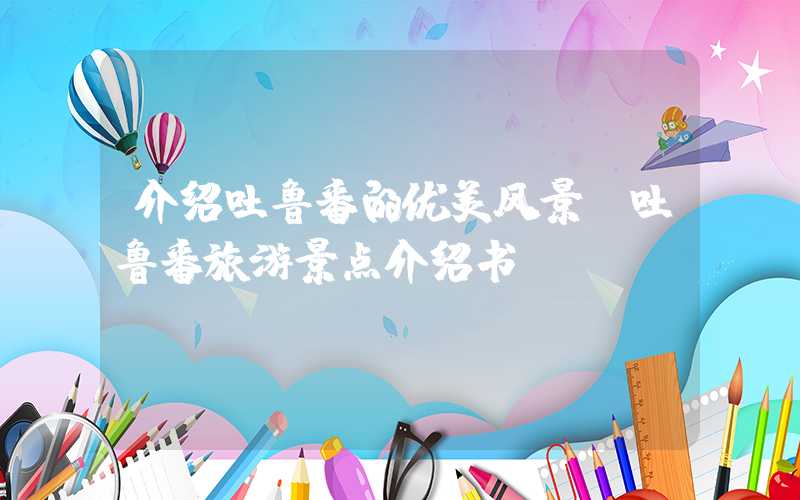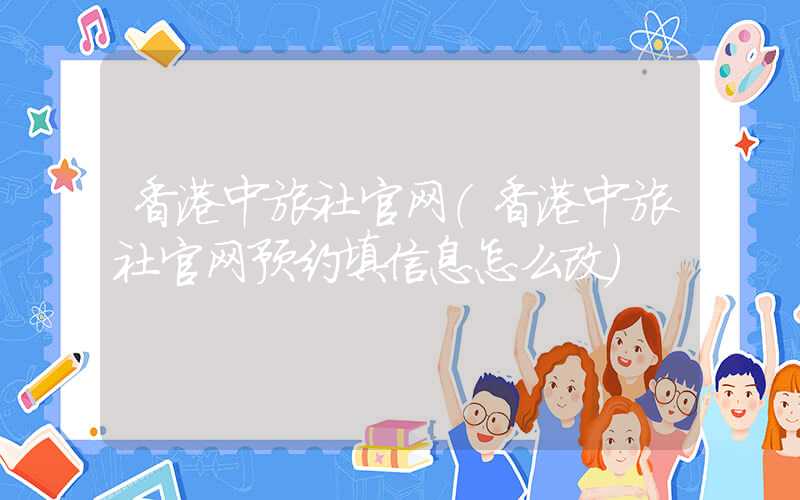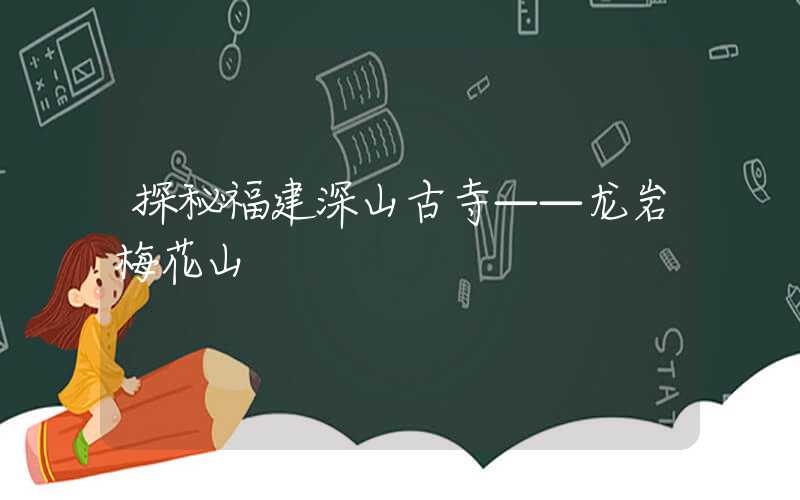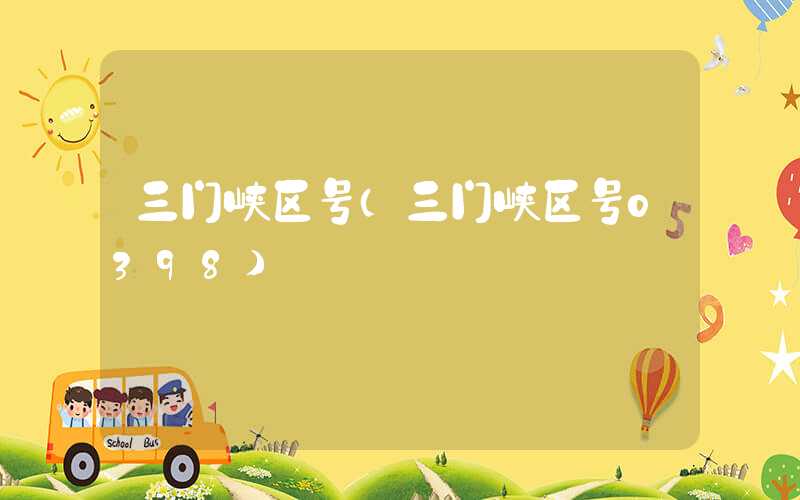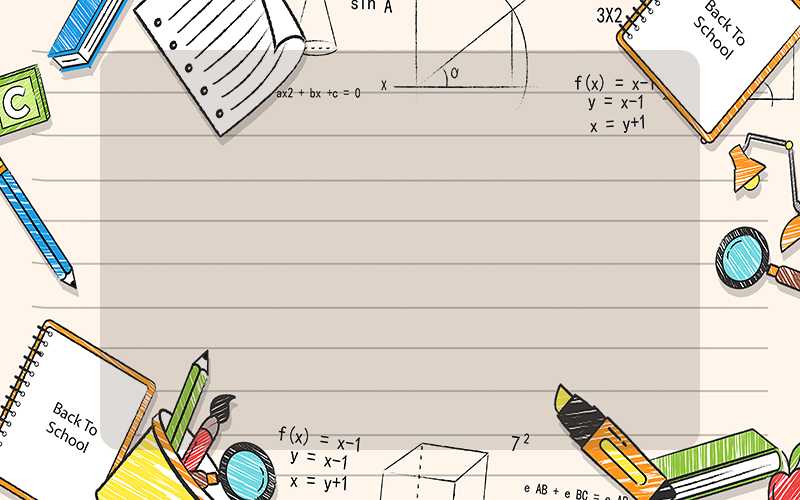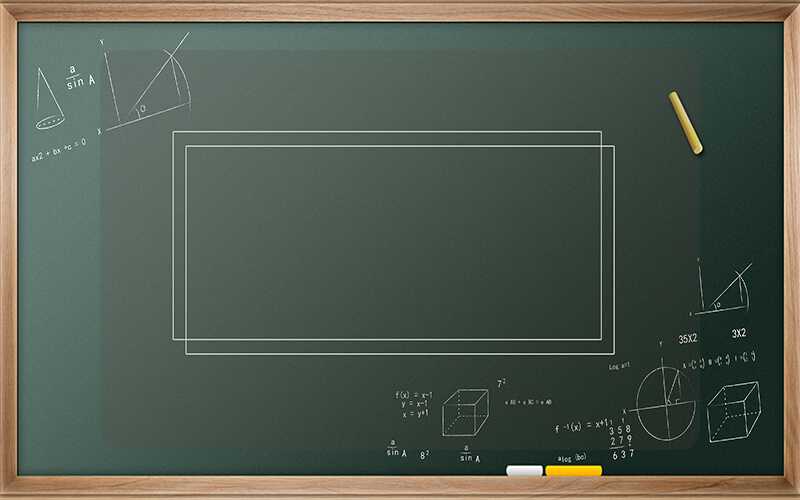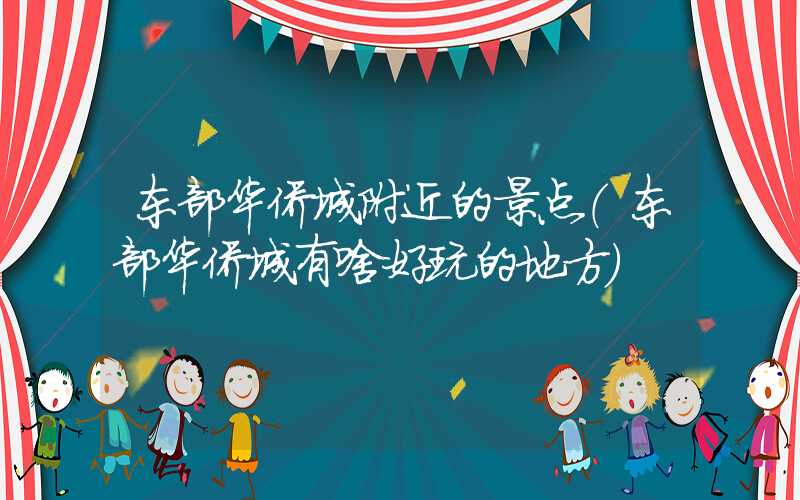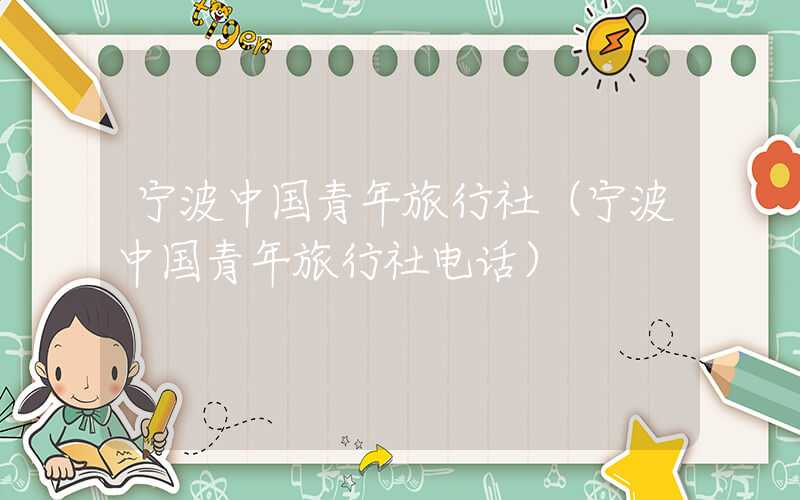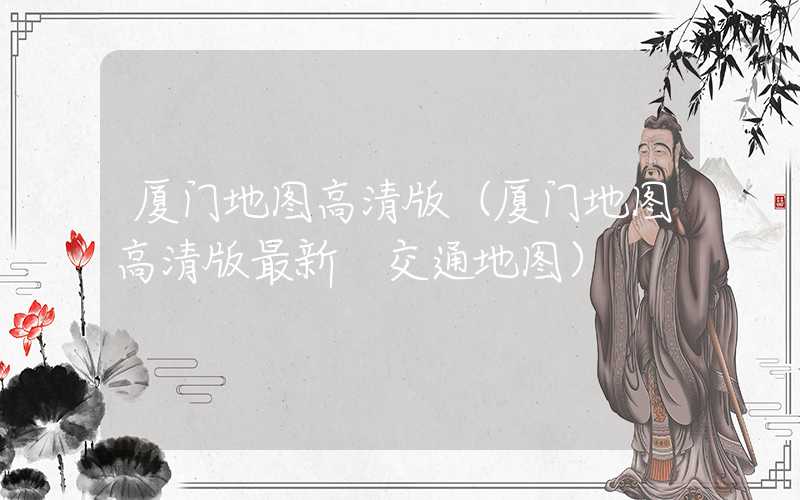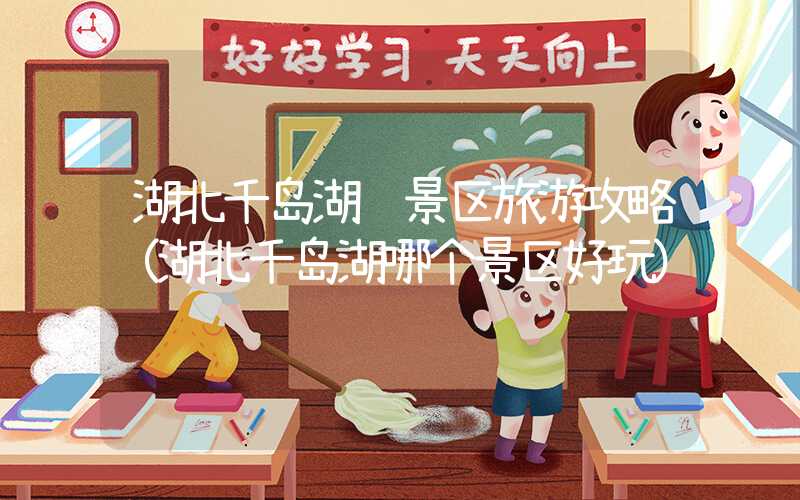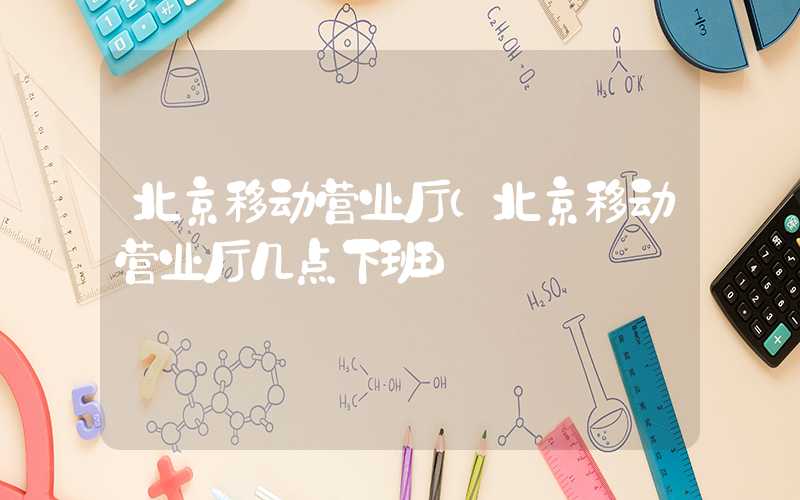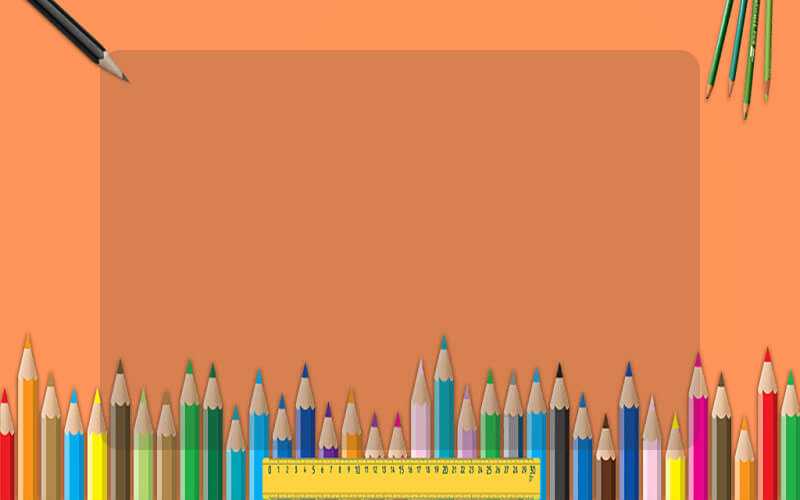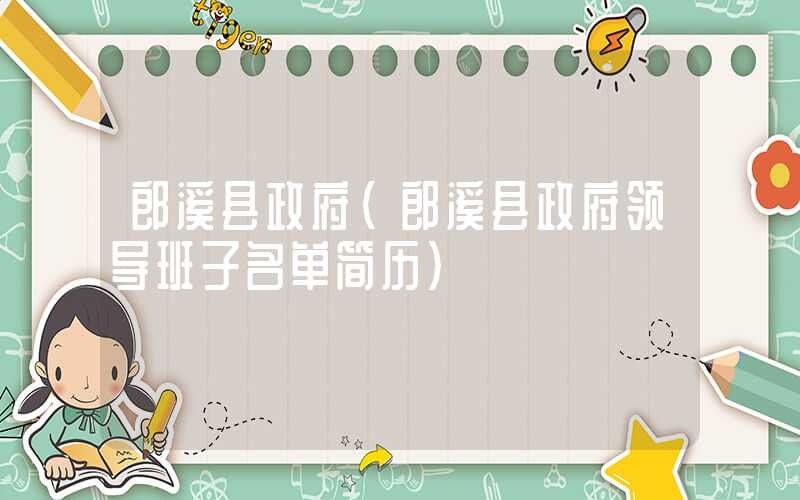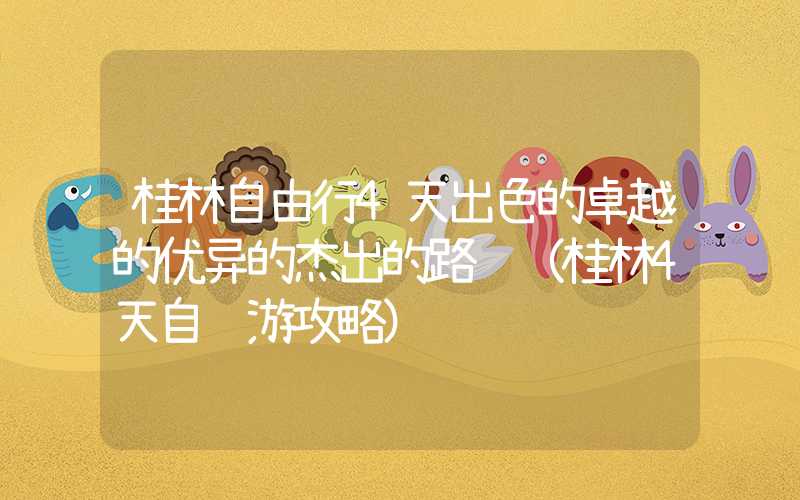博尔赫斯青春类的诗?
博尔赫斯的青春类诗作品主要表现了对青春时光的美好回忆和对逝去时光的深情怀念。他通过对青春时代的感悟和思考,探索了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他的诗歌中,青春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它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博尔赫斯在诗歌中表现出对青春的独特理解和感悟,这些诗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还充满了美妙的诗意和艺术价值。
1、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2.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如何理解博尔赫斯说:“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
这句话的出处分别出自博尔赫斯《七夜》(陈泉译本)129页和《博尔赫斯访谈录》(西川译本)250页。
翻译过来是说:玫瑰开放了,它没有理由地开放了。访谈录的翻译是:玫瑰无因由,花开即花开。
《七夜》的这一处的用法要说明的是:美感是一种肉体感受,一种我们全身感受得到的东西。它不是某种判断的结果,我们不是按照某种规矩达到的,要么我们感受到美,要么感受不到。
《访谈录》的用法是:史蒂文森的诗歌不需要什么过多的解释。他的诗歌是自足的。
我用什么留住你博尔赫斯原文?
原文如下: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先辈,人们用大理石纪念他们的幽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边境阵亡的我父亲的父亲,两颗** 射穿了他的胸膛,蓄着胡子的他死去了,士兵们用牛皮裹起他的尸体我母亲的祖父——时年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名士兵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幽灵。
我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涵的一切悟力、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或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你对自己的解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的真实而惊人的消息。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
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献给贝阿特丽斯•比维洛尼•韦伯斯特•德布尔里奇》(节选)
博尔赫斯的诗玫瑰即玫瑰,出处?
出自其诗集《深沉的玫瑰》
《玫瑰》
在我歌唱之外的,
不谢的玫瑰
那盛开的,芬芳的
深夜幽暗花园里的玫瑰,
每一个夜晚,每一座花园,
借助炼金术从细微的
尘土里重现的玫瑰,
波斯人和阿里奥斯托的玫瑰,
那永远无可比拟的,
永远最出色的玫瑰,
鲜嫩的柏拉图的玫瑰,
在我歌唱之外的,炽热而盲目的玫瑰,
不可企及的玫瑰。
另一个人博尔赫斯逐段赏析?
解读《另一个》
《另一个》里面抒发的那种复杂情绪是博尔赫斯在创造作品时的真实写照。两个博尔赫斯是两股相对突围的力,他们在中间地带奇迹般地汇合,共同营造了艺术的境界。从中我们可以感到那种微妙的双向沟通,也就是感到日常体验如何转化成艺术幻境,“无”又是如何转化为“有”。所有的体验都是双重的、矛盾的,又是同一瞬间发生的。
故事一开始,“我”被命运从沉睡中唤醒,于恐惧中看见了“他”。他是我在目前的清醒状态中要排除的人,因为这个活生生的、世俗的人,这个闯进来的、身上载有历史的人会告诉我,我只是他的梦中出现的人,他是通过做梦得以闯到这里来的。这也等于告诉我,我只是一个影,这是最令我恐怖的宣告。但他又是我排斥不了的,因为他是铁的存在——我的过去,于是一场排斥与反排斥的心理战拉开。
此处令人想起人在创作中要排除日常体验的企图之根源。因为未经升华的日常体验在纯艺术中的出现等于宣告了艺术的不真实。当然一切艺术的来源终究又是世俗的体验,排斥与依存是同时的,作品就在这过程中诞生。
接下去我举出很多自己从前生活的例子 (那也就是他的生活),想以此来证实自己不是一个影子。但他的一句话就把我弄得很沮丧,他认为自己此刻是梦见了我,人在梦中总是相互确信自己是了解对方的,所以我举的那些例子不过说明了一切均是一场梦,并不能证实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他在此处道出了艺术的虚幻本质,那便是我的本质,我无从反驳他。但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坚持,我明知自己此刻清醒,却假设自己也在做梦,我要求他承认这个梦,我想如果他承认了的话,我就有了立足之地,我内心焦急,不愿被悬在半空。
他并不关心承不承认这个梦,或者对他来说,人在梦中无法“承认”梦。他关心的是这场梦的结果,他希望通过做梦达到一个非凡的高度,将日常体验提升,从而最后弄清梦幻将把他和我带到哪里去。我知道,我只有在此刻的清醒状态中,也就是从深层的黑暗中浮出来了之后,才会感到那种虚幻感的折磨——因为我看见了面前的自我 (他)。
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他只有通过做梦,抛弃世俗日常,才能看见我,我在这遭遇中却永远别想用世俗来证实自己。我这个影子痛苦地扭动,将他的未来预告给他,但他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感兴趣,那是他做梦时必然会知道的事,只除了一件事。此刻他所有的感觉都集中在奇迹本身上头,他嗅出了凶兆,一副可怜相 (也许周围的暧昧氛围令他不安,也许他模糊预感到了自己未来的终点)。
接着我向他提到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激动地赞美了几句之后,却又变得淡然了,大概因为他在梦中,情感的记忆就消失了,他要达到从未有过的 (而不是已有的)体验。
在那种体验中,他推崇一种抽象的情感,他要赞美所有的人,不论善恶,他急于将自己的情感升华。我的体验同他相反,我关心的是具体的人,如果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某个具体的人 (例如面前这个儿子一般的亲人)身上,赞美就不会被抽空,并且不显得虚假。看来我和他是无法相通了。
然而反过来想,我同他在此时此地的遭遇不正是一种沟通吗?我们的谈话直接在艺术本质的层面上进行,双方的各执己见正好是本质的矛盾所致。我们在不可重复的奇迹中领略着历史,内心越来越单纯。我把“未来”灌输给他,让他摆脱尘世,感受一回幻境的纯净;他把“现在”的质感带给我,让我在虚幻中“存在”一回。渐渐地,我和他都明白了,这正是艺术创造的奇迹,不能理解的奇迹。奇迹没有记忆,每一次的产生都得从头开始。
梦终究要做完,他会回到世俗中去,我会重新沉入地底。我还要做努力,我向他朗诵了雨果的永恒的诗句,他感动了,沟通似乎达到,我们在永恒的瞬间里完成了双重的排斥——他的世俗记忆和我的虚无感。可惜这样的瞬间马上就消失了,接下去讨论惠特曼的诗歌时,我们之间又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他作为一个做梦者,强调惠特曼的体验的真实性,我作为一个清醒者,强调诗歌激情中的虚幻性。也就是对梦中人来说,诗是真实的,对醒着的人来说,诗是虚幻的。
我和他都感到了我们之间隔着的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仍然焦虑和恐惧,但一切都清楚了:这种相遇是命中注定的,他的闯入就是我的浮出,我们两个才能合成那完整的一个,他通过梦见我而实现他的本质的存在,我通过看见他而成为具体的人,否则他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只是没有实体的影。
关于博尔赫斯简介和博尔赫斯介绍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http://www.nielie.com